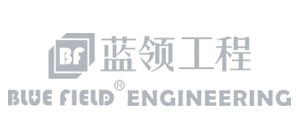- 地址:浙江省余姚市有色金属材料城5栋1号楼
- 联系电话:0574 - 62682960
- 业务咨询:15888536288 Mr zhou
- 公司邮箱:fc@techblue.cn
- 公司网址:www.techblue.cn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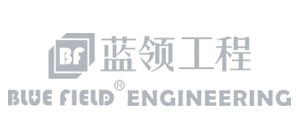

| 东方设计学的哲学思考 | |
| 2016-07-14 浏览次数:1699 | |
|
现代设计体系进入中国大陆是近三十年的事,尽管我们在引进吸收过程中,其理论与方法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随着经济全球化,以及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日益短缺,许多经典设计理论面临着重大挑战,有识人士把目光转向东方寻求发展的新思路。事实上,东方智慧在当今政治、经济、商业等领域展示了独特的魅力。作为科学与人文之外“第三种文化”的设计,需要改变科学至上、功能主义的设计观,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心物一元”等设计理念将在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环境等要素复杂性中赋予新的价值。 1 心与物的融合 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,我国的知识体系和教育基本上沿用了西方的主流体系。这个体系分为两大部分:即理性的科学技术,和以人的存在、价值、实现为宗旨的人文艺术。这是自古希腊时期开启的文化传统,最早的学术研究探索大都以神和上帝的名义展开的,宗教、神话、医学、化学等知识共为一体。到了中世纪,科学成了逻各斯(Logos)的智辩和形而上的释道工具,试图用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。文艺复兴运动唤起了人的主体意识,开始探讨现实存在的“我”与另一个未知的、隔绝的“物”之间的关系。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开启了“心物二元”的思想:精神与物质是相互独立的实体,任何一方都不能还原为另一方,它们各自服从于精神的或物质的规律。 如果人文代表心,科学技术代表物,在商品经济的驱动下,心物呈现出“二元对立”的趋势,造成了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单向度发展。在科学理性主义“绝对秩序”的作用下,情感、幸福、伦理、梦想等构成“人生价值和意义”的因素被忽略。而科技所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,使人相信其重要性的同时,把科学作为衡量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的观念,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。与此相对的人文艺术则将商业社会出现的拜金主义、贫富分化、环境污染、资源枯竭等危机归罪于理性的科学精神。科学和人文这“两种文化”的背离,在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已经成了难以逾越的“鸿沟”,也影响到了发展中的现代中国。 在如何融合心与物,科技与人文如何平衡发展的问题上,西方出现了各种影响深远的思潮。本世纪初对“设计”的重新诠释和定位在“心物融合”上具有重要的价值。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探索各种事物的本来面目,了解其基本属性和客观规律性。其中包含两个方面,一是探索事物是怎样的;二是研究事物应该怎样,而“应该”的诉求就要涉及到人的愿望、爱好、要求等等。这个过程仅靠科技本身解决不了,需要人文精神。将两者融合在一起,并能提出可以被评价、检验的对象物,这个工作就是“设计”。如果说科技回答“如何制造一个产品”的方法论问题,设计则回答“制造什么样的产品”的问题解决型问题。在当今科技信息发达的社会里,产品的制造技术可能不是大问题,设计什么样的产品才能满足市场需求成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。这也是目前中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遇到的问题,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设计服务业,在很大程度上是让国内制造业提升创新能力,这种能力就是设计力。《2001汉城工业设计家宣言》把“设计”诠释得更为明确而深刻:“设计应当通过将‘为什么’的重要性置于对‘怎么样’这一早熟问题的结论性回答之前,在人们和他们的人工环境之间寻求一种前摄的关系;应当通过在‘主体’和‘客体’之间寻求和谐,在人与人、人与物、人与自然、心灵和身体之间营造多重、平等和整体的关系。”[1] 苹果手机的设计诠释了这些理念:通过“触觉”让大众通过扎扎实实的“触感游戏”完成了“键盘对话”,使得“对谈”以类似体验的方式展开,改变了过去那种基于传统文本的线性叙事方式。正是这种体验逐步,改变了人的认知途径和认知结构,找到了技术与人的内心需求的融合点。通过“物”的方式让大众真切地感受到“心”的体验是什么。这种融合心与物的设计,既不是科学,也不是艺术,而是独立于两者之外、相互不能替代的第三种文化。[2] 2 工具性与悟性文化 “心物二元”源于西方传统的自然观,认为自然是无目的的,人是有目的的,人是宇宙的中心。主体地位的确立,就有理由向自然索取。工业革命以后,随着批量生产和商品经济需求催生了现代设计的发展。如果说莫里斯在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中的主张,给现代设计注入了将艺术之美带进生活的新鲜血液,那么之后的德意志制造联盟和包豪斯的“标准化”、“功能主义”,以及美国的“商业设计”等思潮,现代设计逐步沦为科学技术和商业社会的工具,为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“随着工具理性的自大和膨胀,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过程中,设计的本质也在逐渐滋长强势的武断和自以为是的粗暴。使得设计的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,以至与出现设计的霸权,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、控制人的力量。”[3]从哲学家拉美特里(Lamettrie)的《人是机器》,到建筑大师柯布西耶(Le Corbusier)的“住房是居住的机器”,都是设计工具论的典型代表,直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才开始对工具性的设计观提出了挑战。 认识论与方法论密切相关,对设计方法论的探索曾经借助了科技的理性模式和艺术创作模式。上个世纪,从包豪斯“把劳作的世界与艺术家们的创造结合起来”的教学模式[4]、西蒙 (Herbert Simon)的“研究人为事物的设计科学” ,到舍恩(Donaid Schon)的“设计师是反省的实践者”等等,试图探索出科学、理性、系统的设计方法,但没有出现令人信服的、适用于现代社会、可以指导实践的设计方法论。原因是:设计是一个反复的、非线性的过程,通过不确定的问题形势逐渐构筑问题及其解答。所以,设计不是一个知识提取和应用的过程,设计根本就不可能被纳入某种单一知识逻辑框架。无论是观念,还是方法,设计需要从“去工具性”中回归到本体。 现代设计根植于西方哲学思想和商品经济社会,为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。然而,体现“工具理性”的现代设计时常呈现出与“价值理性”的矛盾。“最终扼杀了文化的创造性、丰富多彩性,使文化成为了一种工业文化、单面文化。”[5]处在引进、消化、吸收阶段的中国设计和教育界,需要改变三十多年来被动的设计思想消费者姿态,自觉创发东方设计思想,建立更为健全的人造世界新秩序。 东方文化是一种悟性的文化,悟性文化适合于研究非常复杂的问题。设计作为创造“人造世界”中担当起沟通心与物的桥梁,需要综合判断才能理出条理。设计中的很多事情不是割裂、孤立的问题,不能以简单的形式逻辑推演加以解决,可以将东方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。只有这样,才能不再局限于后发模式,实现从设计理念和方法的根本性创新。“光明从东方来,法则从西方来”。 [6] 东方之所以带来光明,是因为东方思想指明了人类发展的根本方向。 3 东方观念与设计 由于观念的不同,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。东方思维方式特征是直觉的、整体的、模糊的、体悟的和模拟的;而西方的特征是逻辑的、分析的、精确的、抽象的和演绎的。手机的“滑动解锁”被喻为“禅”的设计,是将“逻辑性的科技”与“直觉体验”完美结合。在科学、理性、秩序不断被强化的现代社会,天人合一、心悟、格物致知等东方智慧越来越受到设计界的重视,这些思想可以为创发东方设计学奠定基础。
1)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
2)心领神会的思维方式
3)身心体验的感悟能力© www.dolcn.com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在吸引全世界目光的同时,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再次引起世人兴趣。独立于科技和人文的设计同样需要运用东方智慧注入新的活力,将天人合一等东方智慧在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环境等要素复杂性中赋予新的价值。我们需要改变几十年来纯粹被动的设计思想消费者姿态,创建适应社会创新范式的东方设计哲学和设计方法。然而,东方设计学如何构建?
参考文献
|